阅读:0
听报道
文/玉照
女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越来越醒目地凸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书写主体的形成与80年代深圳等地区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是新时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城市扩建和重组的内在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打工者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突出和醒目的外在标志。事实上,中国女工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并非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化之初,中国女工就已经作为第一批参与中国现代工业的主体,开始受到关注。从封建社会结束到今天的一百年间,考察中国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承担更多的角色的过程中,上海棉纱厂和深圳的现代化工厂是两个重要的空间意象。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刚刚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在这场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棉纱厂在其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深圳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又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空间意向,在这个空间中,无数的打工女孩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注脚。

一、上海棉纱厂女工的阶级抗争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曾指出:“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棉纱织厂=新工人阶级。”和西方近代工业化一样,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棉纱厂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主体。并且,在中国,棉纱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同时它也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社会运动的主体,工人阶级。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民大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都是建立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壮大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这场社会运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主体就是中国女工,艾米莉·洪尼格在《姐妹们与陌生人》中曾指出“棉纱厂女工曾代表上海无产阶级这一声名卓著的群体总数的三分之一。”
自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开始,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就构成了劳工史研究的重点。因此,在对中国女工的研究过程中,从阶级抗争的视角对中国女工进行分析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女工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中国女工确实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海女工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关联。因此,在中国理论视野中,中国女工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被置于传统阶级视角下进行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最初的组成部分,中国女工构成了中国革命话语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抗争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女人长期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上,而很少参与到公共生活领域之中。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刚刚起步的上海棉纱厂中诞生了一大批女工,这些女工开始摆脱传统家庭的桎梏,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走入社会。工厂的工作让女工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家庭以外的生活世界,随着女工越来越多地加入工会、中国共产党等专门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女工开始慢慢超越传统的认知,并在集体行动中逐渐培育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尤其是五卅运动时期,上海的工人们罢工频次不断提高,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罢工要求亦不在少数。洪尼格还特别指出,根据当时上海社会局发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大量的纱厂女工经常参加罢工,实际上,女工经常构成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而且,由于上海工人的大多数以及最具战斗力的工业工人之一是女工,因此有理由推断出女工构成了罢工工人的主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规模较大,但是女工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则很难判断,由于当时女工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甚至不识字,宣传革命、阶级斗争的文章、思想很难在女工中得到较好传播。
回溯女工参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女工这一社群中,比较明显的是因地域、文化等的分化,而阶级的分化则往往体现的并不明显。相较于参加工会,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女工更多地参加姐妹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组织,与工会的政治性不同,姐妹会更多产生于一种日常生活。这种组织更多是出于一种相互帮助、相互保护的日常生活关系建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诞生于女工日常生活中的组织后来为共产党所改造,成为共产党团结女工的重要组织,从而间接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运动领袖。尤其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的罢工运动已经非常不同于20年代女工罢工的被动性,此时的女工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抗争意识和革命意识。总之,中国女工的抗争和阶级意识并不能单纯地描述为两大阶级之间对立的故事,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女工参与的工人运动十分有限,她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其生活轨迹仍然与其农民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女工真正积极参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的内战时期,女工的这种阶级意识在见过以后也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强调阶级,而弱化乃至否定性别差异,对女性的书写也主要着重于其阶级属性。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改革开放,资本逻辑开始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这种阶级分析话语呈式微状态。和毛泽东时代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在新的叙事话语中,女工们的主体意识则需要传统阶级抗争之外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
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女工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的话,那么今天,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共同支配下,女工们的日常生活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中天然就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倾向,而阶级分析话语中则天然包含着集体主义的指向。今天如果说女工的抗争中仍然包含着阶级抵抗的意味的话,那么这种抵抗只能是一种隐藏的表达,一种理论的想象,相较于政治的诉求,女工们今天的抵抗更多是切己的诉求。
二、后阶级分析时代的中国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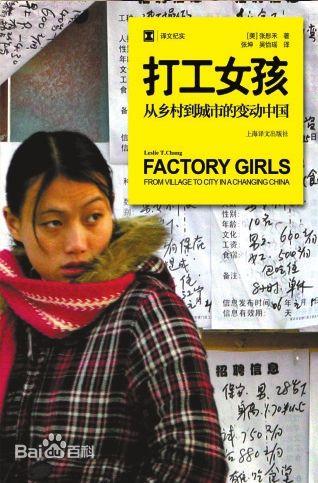
(张彤禾著《打工女孩》书影,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成为主人的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是对异化的克服,是工人的主体性向自身的回归。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形成,工人阶级逐渐向打工者转换,打工意味着一种新的劳动剥削的形成。和毛泽东时代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今天的打工者从某种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道路上去。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阶级不断被消解,对抗资本的公共行动始终没有形成,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打工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到底有没有一种潜在的,隐含的阶级意识存在呢?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性别的差异性逐渐凸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如果我们仍然能将打工者称作无产阶级的话,今天的打工者群体已经完全没有了针对资本的有组织的公开性对抗。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相比,打工者更多采取的是个体行动,而非集体行动。
不再存在劳资两大阶级公开抗争的情况下,女工们开始寻求新的社群来实现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和身份的认同。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身份变化对中国女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农村生活强调关系性在生活交往中的重要性,而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女工们开始慢慢脱离原有的关系网,离开家乡、父母、亲戚,独自面对资本。乡村和城市生活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换,这种社会交往形式的转变使得适应农村熟人社会的女工并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的生活,或者说身体的城市化并没有立刻带来心理的城市化,资本市场加速了打工者们个体生活的孤立化,但新的关系网并不能迅速建立起来,于是女工们往往倾向于去寻找新的团体,重建一种熟人的关系网。这些打工者群体普遍比较重视同乡、血缘等因素,打工者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开始重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关系网。家庭关系、族群关系等对女工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棉纱厂女工一直到今天的深圳打工者,地域关系网对他们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洪尼格甚至认为女工之间的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女工对不同地区女工的敌视更甚于对资本家的敌视。潘毅也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外资以及其他类型的工厂中,打工妹们仍然是被仅仅包围在同乡和亲属网络之中的,尽管这些网络经常是被重新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但是它们却给打工妹们提供了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支持。”之所以会出现同乡会等诸如此类的关系网络,一方面是因为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和自己相近的群体,从而产生一种抱团现象。所以同乡会等就成了女工们在城市依附的重要组织形式。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女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并未带来同步的身份认同。和欧美无产阶级不同,中国女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女工还和农村存在着十分强烈的联系,他们对自身城市无产阶级这一身份认同感并不十分强烈,所以他们借助同乡会的形式来实现在城市与农村身份之间的转换。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都很普遍。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来看,这种从农民到工人的无产积极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必然结果。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工人们普遍面临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这一空间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但是,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不同,中国的农民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过程中,并未完全实现身份的转换,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无产积极,而是转换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体。农民工们是今天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以也很难用马克思的阶级话语对其进行分析。马克思的对工人积极的话语分析的经验主要来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经历圈地运动的农民很快转化为无产积极。但是中国工人积极的形成和英国的境况不同。工人阶级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只能是农民工,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如果说,马克思批判英国的资本主义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签署了形式平等的契约关系,而实质上却不得不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那么在中国的社会中,由于制度的约束,农民工甚至无法得到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因为农民工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临时性,他们无论如何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身份认同始终还是农民。这就意味着,相较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的异化,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面临着更多一重的异化,那就是实际的城市生活状态和农村身份之间的异化。
对于女性打工者而言,这种双重的异化尤其明显,当下的女工处于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相联合的大背景之下,国家和资本联合共同形成了对打工女孩的新的压制权力。打工女孩随时面临着城市与乡村,家庭与工作之间的二选一问题。首先,是选择在家侍奉父母,还是外出打工。其次,即使是外出打工,到了一定婚假年龄也面临着是回老家结婚生子,还是继续留在城市打工。而结婚以后的打工者同样面临着是否继续出来打工的两难选择,打工女孩们始终处于家庭与工作的纠缠之中。不论任何时代,性别政治始终是女工们不得不抗争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当年的上海棉纱厂女工如果说是被动地融入的话,那么如今的打工女孩则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打开国门,这一背景之下,打工女孩这一新的社会主体又重新被创造出来。就像当年的上海棉纱厂女工从来不曾真正见过上海繁华地带的霓虹灯一样,这些新的打工者群体一样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中国上层社会的灯红酒绿。现如今大部分打工女孩,仍然是城市、农村之外的第三种公民,她们一般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很年轻时就去大城市打工,到了一定年龄就回家相亲结婚,离开城市。当然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女孩结了婚后和丈夫一同外出打工。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的临时性也就合法化了。他们一样长时间的工作,尽管相比较当年的棉纱厂女工,境遇有了一定的改善,大部分农村人认为出来打工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事实上,这些多挣的钱完全是以透支自己体力为代价的。
社会在发展、进步和现代化过程中,会经历种种阵痛,但社会底层的牺牲,往往是最大。今天的女性打工者尽管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20年代的棉纱厂女工那样,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在整个市场化、资本化的过程中,这些打工者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看似自由的打工者生活,事实上并不自由,不论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还是从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女工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进行分析,其背后隐藏的都是一种潜在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压迫。
文章原题为:中国女工的性别政治——从上海棉纱厂女工到深圳打工女孩
(图文编辑:陈锴)
★本文由作者授权,首发于微思客,转载请联系作者或微思客团队,并注明: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6),并附上本网页链接,作者:玉照。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