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死亡之吻?
郭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2年开始设立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止2014年6月的第38届世界遗产年会,世界上共有世界遗产1007项,其中文化遗产779项,自然遗产197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1项。通常认为,名录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意大利记者、学者马可·德·埃拉莫(Marco D'Eramo)近日于英国《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上撰文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是死亡之吻(the kiss of death)。

(《新左派评论》第88期封面,图片来源:)
埃拉莫认为,一座城市一旦被贴上“遗产”的标签,原本的生活便会变质。所谓的保护,实际上是一种防腐(embalm),是一种冻结(freeze):因为改变不被允许,所以时间从此静止,一座城市也自此失去了生命。作者并没有否定对于一些纪念碑式的建筑的保护,但刁难地问了一句:如果雅典卫城在公元前450年就被保护起来了,那我们也就不会看到它之后那些同样辉煌的建筑了。同理,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穿越到16、17世纪的罗马,一定会被当时方兴未艾、正大兴土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吓坏的。
阔别家乡30年的作者不久之前返回了这座中世纪古城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他发现城墙中连一位屠夫、杂货店商、面包师傅都没有。一到夜晚,当那些饭店、纪念品商店关门后,城中找不到原住民的影子:他们都搬到城外的现代公寓中去了。对于作者而言,失去了最原汁原味生活的圣·吉米尼亚诺,充其量就是一部古装电影的布景罢了。

(圣·吉米尼亚诺,图片来源:)
就是所谓“文化遗产”的普遍状况:不再有居民,不再有生活,乡关何处?这一切恰恰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城市因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而成为遗产,但随之而来的商业大潮却使得附着于城市生活本身的独特性消失殆尽。与其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了一个个独特的城市,不如说他们复制出了一个个“四不像”(non-place)。
埃拉莫将这种行为比喻为:治好病的同时也杀死了病人。在他看来,拯救几块砖瓦并不等同于拯救了一座城市及城市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不可以相提并论。保护自然遗产的确可以起到保护生态多样性的效用,但是,目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却适得其反。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旅游业。
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任由城市肆意发展,那么那些古老的建筑将被银行大楼所取代。但埃拉莫认为,古老的建筑与银行大楼之间的对立并不成立,因为前者支持的旅游业与后者代表的金融业都是强劲的印钞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埃拉莫将文章的后半部分以“贩卖真实性”(Selling Authenticity)为题,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旅游业进行了一次不留情面的分析。他指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产的“品牌”——纵容旅游产业在市场上将一个个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变现。埃拉莫引用了迪安·麦克卡奈尔(Dean MacCannell)在《旅游者:有闲阶级新论》(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97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经典观点做出的重要反驳:艺术品的“灵光”(aura)恰恰是在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开始之后——而非之前——才出现的。具体言之,文化遗产的“灵光”是在它被无限度地商业复制之后才出现的,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恰恰为此提供了认证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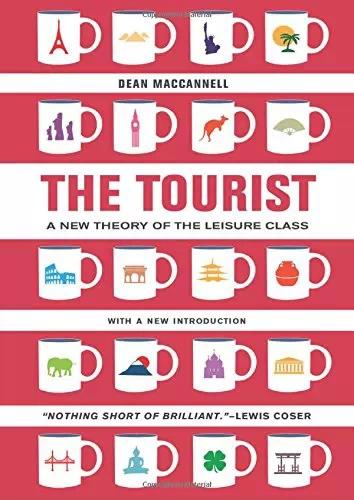
(《旅游者:有闲阶级新论》封面,图片来源:)
作者进一步分析,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不是旅游业的根由,它更像是为旅游业“正名”、实现其合法化的一枚印章,给这项工业罩上了一件意识形态迷彩服。因为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存在,我们不再意识到旅游业背后敛财的事实,我们在保护文化的大旗下渐渐无视旅游业的对文化造成的伤害。埃拉莫说,文化与旅游业、遗产保护与资本从来不是对头:他们暗中联手。
作者最后指出,这些因为成为文化遗产而失去生命与个性的城市仅仅是今日普遍的城市问题的一个极端表现。后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调功能分区,城市中的每一个区域有且只有一个功能,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住宅区”、“金融区”这类区分。但是,功能分区与人类建立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城市之所以让生活更美好,是因为它交融并会了多种多样的人类活动(places of interconnection and articulation between diverse human activities)。埃拉莫指出,任何一个依靠单一工业的城市,都注定灭亡。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许多城市成为“观光区”,使许多城市开始单纯依靠旅游业生存,所以无异于一次城市毁灭(urbicide)。正因如此,埃拉莫赋予本文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式毁灭”(UNESCOcide)!
埃拉莫早年在巴黎跟随当代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学习社会学,因而深谙经济-金融资本对文化资本的绝对控制,行文运笔间无处不露出左派的锋芒。不可否认,他的观点极具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仅仅停留于理论演绎,而无论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业甚至城市规划都远非纸上谈兵。现实中的枪林弹雨比起简单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恐怕要复杂得多。埃拉莫批评文化遗产保护让许多城市“有形无神”,但倘若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许多古城连“形”都没有了。近些年来,文化遗产保护界关于“活态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开始注重在保护物质遗产的同时,同时保护原生态的生活,从而让文化遗产“形神兼备”。
【参考文献】Marco D'Eramo, UNESCOcide, New Left Reivew (88), p. 47-53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推送,首发于“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如需转载,请附上本说明,并附上本网页链接。作者郭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民间文化论坛》通讯员,曾任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志愿者。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