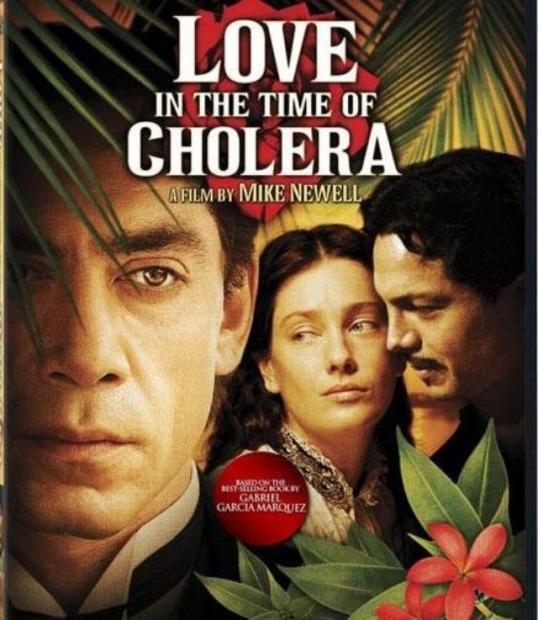
爱情是一种病
文/段善策
暗恋、初恋、失恋、单恋、三角恋、露水恋、婚外恋、老少恋、黄昏恋、柏拉图式的精神恋、肉欲极乐的床第恋、狂热的恋、反省的恋、浓浓的恋、淡淡的恋……由拉美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几乎穷尽世间一切爱情的形态,堪称一部关于爱情的百科全书。
爱情与死亡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当我在猜测这会不会是一部肤浅的爱情幻灯片的时候,它以不断地震撼颠覆了我对爱情电影所有的刻板印象。马尔克斯告诉我们:恋爱的感觉其实和霍乱的症状相似,死亡以殉情、憔悴和衰老的形式隐藏在失恋之中,失恋的体验就是一种走向死亡的体验。影片主人公阿里萨苦苦等待爱情五十三载而不得,直到生命的尾声却意外收获了爱情。经历五十三年的漫长等待,看到的却是“公主”早已臃肿的身体时,这个见识过622个女人的身体的欢场老手竟然像孩子一般紧张害羞了;经历五十三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进入“公主”七十岁的身体时,这个睡过二十岁姑娘的老头竟然激动地抽噎起来。
这是一种行将朽木前爱情归圆的满足,这是一种爱情与死亡的赛跑中终获胜利的庆幸。在这场时间做裁判的战争中,死亡长期占据着上风,但最终的胜利者是爱情。于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我意外地发现:爱情和死亡是如此接近。
爱情和死亡是如此接近。“弥留之际的床榻是特定的文学领地”,失恋的身体也是文学热衷铭刻的场所。在文学的世界里,爱情和死亡首先是景观,制造神圣的时刻,供人瞻仰、回忆和遗忘。
爱情和死亡是如此接近。它们首先是一种人类发明,一种语义学上的命名。在动物的历史里,没有爱情的历史,只有交配史;也没有死亡的历史,死亡只是一瞬的事,只是繁衍史上一个周而复始的环节而已。只有在人类那里才有“性兴奋的连续性”,随后诞生了永恒的爱情;只有在人类那里才有对死亡持续的恐惧,随后诞生了疾病和医学。
爱情与文明病
“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发出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在影片《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霍乱不仅是被来自西方的知识权力结构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且还特指一群人——一群属于肮脏、贫穷和愚昧的第三世界的人。霍乱成为驯服和殖民他们的一种手段。
达萨疑似感染了霍乱,父亲请来巴黎留学回来的乌尔比诺医生为她诊断,乌尔比诺没有征询达萨的意见就剥开了她的上衣坦露酥胸,并且面颊贴着她高耸的双乳实施听诊,达萨的羞赧和自我保护在他的专业姿态面前不堪一击,投向侧旁期许援手的目光看到的也只是父亲低头捂脸的默许。她意识到抵触是徒劳的。不仅如此,受过西方教育的达萨还明白在科学面前还应该放下本能的羞耻感,因为在西方医学观念中,病人的身体是一具去性别化的治疗对象物,因此病人任何道德上的不配合不仅显得自己愚昧无知,而且延误病情。于是她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愕和害羞不让乌尔比诺医生察觉,并进而努力使身体去适应现代文明的凝视和检查。而敏感部位被凝视和触碰带来的快感使得她的眉梢和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微上扬。这隐喻了第三世界面对西方征服者,从被冒犯到被征服的复杂情感结构。这种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许多第三世界的电影里都有所表现,比如刚刚上映的《太平轮》。严泽坤听诊时让周蕴芬解开衣襟,对于习惯了日据时期形成的西医文化的本省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但对于“隔帘问切”的中医文化中成长的周家人而言,这就是一种冒犯。
医学利用并制造恐怖来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医学话语抗衡,包括爱情。鉴于爱情的潜在威胁,感染者必须被隔离。因此,在影片前段,因为鼓励爱情,达萨的姨妈被撵走;因为坚持爱情,达萨被押走;因为沉迷爱情,阿里萨被送走。因此,在影片尾声,为了守护爱情,阿里萨和达萨只能以感染霍乱为名自我隔离。从少年时“爱情万岁”的莽撞到垂老时“我们有病”的从容,看尽五十三载潮涨潮落,他们终于明了爱情在这个世界被诊断为一种病,要么治愈它,要么坦然接受它。
爱情、婚姻与第三世界的历史
西方文明殖民下的哥伦比亚失去了像亚马逊原始森林一般供爱情的蔷薇自由蔓生、开花结果的空气和土壤。爱情和婚姻在这个社会里构成一种紧张而畸形的关系。婚姻成为身体经济学的一种修辞策略,爱情就像舒伯特小夜曲,它是询价前为促成交易而制造的浪漫氛围,它是一个不错的点缀,但喧宾夺主是不被允许的。达萨父亲对待两位潜在买家的不同态度也很好理解。对女孩身体的监护人而言,让背负着道德(失贞的罪恶)和疾病(婚前性行为的卫生风险)诅咒的姑娘们穿着束胸、扎腰、蓬撑裙,制造丰乳肥臀的曲线,欢迎的可不是电报送递员阿里萨这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穷小子,乌尔比诺医生这样的大户子弟才是监护人理想中的座上宾。对达萨的父亲来说,嫁女儿跟卖骡子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将骡子卖给哪个买家的问题上,询问骡子愿意跟谁走是一件可笑而荒唐的事。如果骡子开口说了,那它不是有病就是怪物。谁要是把这当了真,坚持要他尊重骡子的意愿,他一定会像对阿里萨那样毫不客气地亮出腰间的手枪。就这样,19世纪末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哥伦比亚的历史就是一幅“身体被纳入到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
这种历史的卷入感在影片里还有一处更为明显的表现。故事的发生地、这个地处偏僻的哥伦比亚小镇举办了一场迎接1900年新世纪的庆典。在这里,这片太阳神护佑的印加文明的大地皈依了基督的时间版图。就像乌尔比诺医生出轨后忏悔的神祗是圣母玛利亚一样,世俗的、宗教的甚至时间本身都被卷入西方世界的历史当中。对此,马尔克斯采取了一种弱势书写的叙述策略,通过戏仿、间离和反讽的方式抵抗这种历史的殖民。庆典上,镇长以一种救世主的口吻大声向围拢的人群宣布:“即将到来的20世纪,人类的痛苦将消逝!20世纪将给我们带来和谐、和平,也将给我们带来光明!”随着舞台布景上“1900”四个巨大的阿拉伯数字通电后的熠熠生辉,人群一片欢呼雀跃。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核爆炸、冷战……历史已经证明刚过去的20世纪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动荡、最痛苦、最黑暗的世纪。这场憧憬新世纪的狂欢出现在写于80年代的小说里,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无法忽略的是,这场在阿里萨连续痛失情人和母亲之后出现的世纪庆典更加凸显其荒诞和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会在这里那里受挫,但是一般说来,它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步的和决定论的。”
现代爱情也深受这种大写历史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幸福永远在远方等着你,眼前的疼痛、孤独和无助不过是旅程的考验和佐料。然而,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马尔克斯先生再一次跟爱情开了一个玩笑——用性的放纵守护爱的情书。痴情汉阿里萨在漫长的等待中渐渐发现,守护爱情誓言根本不是会写一封充满诗意的情书或者会拉一曲舒伯特小夜曲,而是一场对寂寞漫长的煎熬,尤其昔日的爱人已为人妇。于是,在一次偶然的艳遇后,他开始四处猎艳,用放纵的生活排遣内心的空虚,用性的满足填补爱的匮乏,甚至精神上还开过一次小差——喜欢上一个新婚少妇,过上了一种达萨表妹所说的“没有爱情的‘快乐’生活”。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例行公事”就像铁锈,每多一次,孤独就增加一分。爱情,对于终身未娶的阿里萨来说,是一种比霍乱更为严重的疾病。它损耗着他的身体,更折磨着他的灵魂。
爱情,对围城里的达萨和乌尔比诺来说,也何尝不是一种病。他们的婚后生活总是充斥着由琐事引发的争吵。乌尔比诺认为“婚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安定”。在他看来,夫妻双方在步入教堂前就应该确认自己不会再犯病。而达萨的回应则是“但是爱,没有什么比爱更难”。显然,她认为爱情是种绝症,没得治。
原来爱,真的很凶险,它是一场跨世纪的霍乱,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与死亡体验类似的冒险;没胆最好别上场。
★本文经作者授权由微思客推送,首发于“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段善策,武汉大学影视专业博士在读,如需转载,请附上本说明,并附上本网页链接。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