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根据2017年1月2日DaliyNous网站消息,哲学家帕菲特(Derek Parfit)于元旦逝世,享年74岁。今天,微思客WeThinker传媒重磅推送他的《论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一书中文版《导言》。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巨著。2015年9月,经过译者阮航、葛四友的努力,中译本终于问世。这本被学者布兰德·胡克(Brad Hooker)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称之为“自1874年西季维克《伦理学方法》以来最重要的著作”的巨著,究竟有怎样令人称道之处,让我们跟随《导论》来先睹为快。阅读经典,反思经典,或许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吧。
《论重要之事》导论(节选)
塞缪尔·谢弗勒 著
阮航、葛四友 译
帕菲特这本书处理了实践哲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其论证详实,且极有原创性。本书分两卷,各有三个部分;其核心章节是第二和第三部分,处理的是实质(substantive)道德问题。这些章节源自帕菲特2012年11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三次唐纳讲座。讲座并不包含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六部分所处理的问题。第一部分对理由(reasons)和合理性(rationality)做了一个扩展讨论,为第二和第三个部分的道德主张提供了背景。第六部分探讨的则是元规范(meta-normative)问题。我们在使用规范性(normative)语言来提出有关理由和道德的主张时,就会引出这样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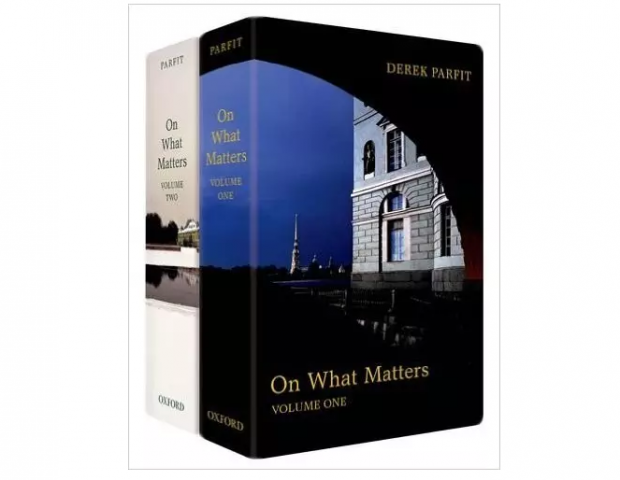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三位对帕菲特的唐纳讲座做出回应的评论者(斯坎伦(Thomas Scanlon)、沃尔夫(Susan Wolf)和伍德(Allen Wood))提供了其评论的修订版。此外,赫尔曼尽管没有参与伯克利事务,但专门为本书写了一组评论。帕菲特在第五部分对这些评论均做了回应。他与评论者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于源自唐纳讲座的那些章节。
帕菲特关于道德的讨论,其目的在于重勘道德哲学的版图。修习道德课程的学生们通常受到这样的教导:后果论者与康德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前者认为,行动的正当与不当(right and wrong)仅仅是其综合后果之函数;后者则通常参考这个或那个版本的绝对命令,从而论证我们具有某些必须履行的义务(obligation),不管这样做是否【xx】能够产生后果论眼中的最优结果。尽管人们公认,不管是康德主义观点还是后果论观点都有诸多的变体和改良,但包括康德主义者与后果论者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定:两者的差别是深刻且根本的。
在本书的第二、三部分,帕菲特试图破坏这个假定,且试图证实:尽管我们习惯于认为两者的立场是相对立的,但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趋同性。首先,对于康德本人的道德哲学包括绝对命令的各种表述以及其他许多核心观念,他做了一番持久而彻底的考察。尽管康德的道德哲学著作,特别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在道德哲学史上已经得到了最广泛的讨论,但帕菲特对这些文本的处理还是产生了大量新颖的观察与洞见。
帕菲特在序言中交待得很清楚,他对康德的态度很复杂,一言难尽。他把康德描述为“自古希腊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235),“短短的四十页却大放光芒,其中给出的富有成效的新观念,比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哲学家提出的还要多”。不过,他马上补上,“不一致性是使康德能取得如此成就的诸多品质之一”。康德的众多评论者都有明确的自身定位——或是作为康德的批评者或是作为康德观点的捍卫者,但帕菲特采取了与他们不同的进路。他把康德的文本当作一座富矿,其中所有的主张、论证和观念,都值得我们就像对待一个卓越同代人的观念那样认真对待。不过,他认为,康德的许多观念需要澄清和修正,有些观念则根本没用了。帕菲特对这些观念、论证和主张做了大范围的考察,让它们经受高水平的检验,这种检验的显著特点在于执着的聚焦和分析的强度。他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捍卫也不是批评康德,而是要确定,我们可以利用康德的哪些观念来取得道德进步。进步才是帕菲特最终的真实目的。正如帕菲特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要修正康德的一个表述时所说的:“【xxi】在学习伟大哲学家的作品之后,我们应尽力取得更多的进步。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有能力比他们看得更远”。(300)
帕菲特辨识出康德思想的若干要素——对于这些要素,帕菲特尽管做了某些重大的修正与补充,但仍认为它们特别重要,也乐于认同它们。然而,他诠释这些观念之内容与含义的方式,往往不同于其他重要的评论者。他对绝对命令的“普遍法则公式”(FUL)的处理,也许最清楚地显现了这一点。如帕菲特所见,绝对命令的这一公式一直受到许多严重的反驳;这使得许多本来抱同情态度的评论者都认为,就作为区分正当与不当的指导原则而言,它对我们帮助甚小。许多重要的康德学者都认为,绝对命令的其他表述更为丰富,也更有启发。

相比之下,帕菲特则看到了普遍法则公式的巨大潜力。与流行的诠释意见相左,他坚持我们“能够使得FUL变得可行”,他主张“这个公式以完全康德式的方式修正后,是……相当成功的”(294)。实际上,他走得非常远,以致认为这个公式经过恰当修正后的版本“也许就是康德自称一直在苦苦寻觅的那个最高道德原则”(342)
帕菲特偏爱普遍法则公式的这一修正版本:“每个人都应当遵循那些每个人都理性地意愿其被普遍接受的那种原则。”这个版本诉诸一种普遍的选择或同意,因此它有资格作为一种形式的“契约论”,帕菲特将其作为“康德式(Kantian)契约论公式”。如果如此诠释,康德式立场就可以与契约论的各种当代版本——特别是那些本身受到宽泛意义上的康德主义启发的各种版本——做比较。罗尔斯诉诸在无知之幕后得选的原则就是一例,尽管他把这种装置几乎只用来为社会的基本结构选择正义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短暂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可以将同样的装置运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原则选择——但从未贯彻下去。尽管如此,帕菲特还是对这个观念做了严厉的【xxii】批评,并断定,就作为一般性的道德论说(account)而言,罗尔斯式契约论的前景远不如斯坎伦所发展的契约论。
按照帕菲特的表述,“斯坎伦的公式”认为“每个人应当遵循无人可以合情理地(reasonably)拒绝的那些原则”。帕菲特认为,至少基于某些诠释,斯坎伦式契约论与康德式契约论是吻合的。因为基于这些诠释最终会发现,每个人都理性地意愿要被普遍接受的那些原则与无人可以合情理地拒绝的那些原则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帕菲特与斯坎伦在这两种契约论趋同的确切程度上存在着分歧,但它们趋同的可能性并不特别让人吃惊。更让人吃惊的是帕菲特对于契约论与后果论之间关系的评价。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康德主义立场与后果论立场之间的对立通常被看作是深刻且根本的。当代的契约论,无论是罗尔斯的还是斯坎伦的,其意旨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于阐述替代后果论的某种强有力理论。然而,帕菲特认为,康德式契约论实际上蕴含了某种版本的“规则后果论”,后者认为“每个人都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其被普遍接受将使事情进展最好”。他强调,每个人都理性地意愿其被普遍接受的那些原则恰恰就是那些“最优的”规则后果论原则。据此,康德式契约论和规则后果论可以组合形成被称为“康德式规则后果论”的观点:“每个人应当遵循最优原则,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每个人会理性地意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原则”(411)。尽管就人们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主张的内容而言,这种立场是后果论的,但就我们为什么应当遵循这些原则的论说而言,这种立场与其说是后果论的,不如说是康德主义的。我们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是因为我们会理性地意愿它们被普遍接受,而不是因为如后果论者所说的,最终重要的就是产生最好的事态。
既然康德式契约论蕴含规则后果论,既然某种版本的康德式契约论与某种【xxiii】版本的斯坎伦式契约论是吻合的,那么三种立场的各个版本就可以组合起来。由此导致的“三重”理论就认为“某个行动是不当的,当且仅当它不容于这样的原则:该原则是最优的,是唯一可普遍地意愿的,且是不可合情理地予以拒绝的。”(413)帕菲特深信,各种可能性的趋同导致:康德主义者、契约论者和后果论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是种错误的看法。相反,“这些人是从不同的侧面攀登同一座山峰”。(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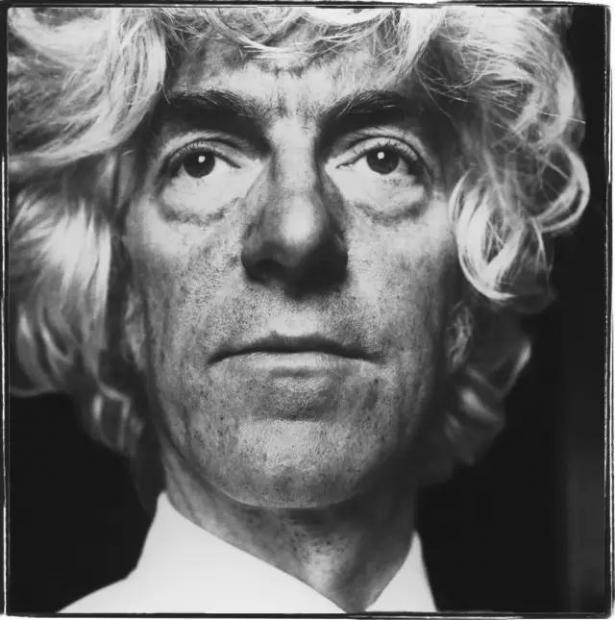
(图片来源:)
帕菲特在发展这种核心的论证思路时,极为依赖他有关理由与合理性的实质性(substantive)主张。人们在想要事物或想做事情时持有何种理由,人们的行动在何种条件下是合情理的或合理的,帕菲特考察的各种理论对此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帕菲特对于这些理论的评价,也就很大程度上在于评价这些不同的主张所具有的力度。不过,有关理由与合理性的主张所具有的争议性,一点也不少于有关正当与不当的主张所具有的争议性。帕菲特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他开始有关道德的章节之前,他对自己有关这些主题的观点做了详尽的阐述与捍卫。
许多哲学家认为,我们的行动理由全部是由我们的欲望来提供的。我们最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它能够最好地满足我们的实际欲望,或者满足在理想条件下我们会具有的欲望。帕菲特把这种基于欲望(desire-based)的看法称之为“主观理论”。尽管无论是在哲学之内还是之外,这种理论都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帕菲特还是相信:它们有着深刻的错误,且他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是毁灭性的。他主张,这些理论不仅具有大量说不通(implausible)的含义,而且最终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这些理论蕴含着:我们理由的规范力量来源于我们根本没任何理由具有的欲望。而帕菲特主张,这样的欲望并不能给我们任何理由。由此,最终,基于欲望的观点的真实含义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行动理由,由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事情是真正地重要的,其意义是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乎任何我们确实在乎的事物。
在拒绝这些“黯淡”的观点之后,帕菲特反过来主张我们应该接受基于价值的(value-based)客观理论。按照这种观点,行动理由是由行动所实现【xxiv】或满足的价值(或者用他的话讲,“使得某些事情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值得做”的事实或“使得结果或好或坏”的事实)所提供的。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话,理由的判断就比合理性(rationality)的判断更为根本。因为在帕菲特看来,当我们对理由或显见(apparent)理由做出回应时,我们就是理性的;而若我们的信念为真,且我们做的事情有好的理由,则我们的行动就是合理的。这与实践理性的许多流行论说形成了对比,例如后者之中有些将合理性确定为期望效用的最大化,有些将实践不理性诠释为某种形式的不一致性。
如斯坎伦文章中的看法,理由优先于合理性的观念也与康德的观点相冲突。对于康德而言,无论是绝对命令的权威还是对其内容的理解都要参考理性的能动性,而不是参考有关“人们所具理由”的某种独立观念。正如斯坎伦所描述的康德主义观点——他称之为“理由的康德式建构观”:“有关理由(确切地说是人们必须看作为理由的因素)的主张必须扎根于人们有关理性能动性的主张,也就是有关人们把自己看作理性行为者相一致而能够采取何种态度的主张。证成(justification)永远不能反过来,即从有关理由的主张来得到有关“合理性要求什么”的主张。
帕菲特像斯坎伦一样拒绝了理由的康德式建构主义,且如斯坎伦所指出的,帕菲特表述(他试图证实会趋同的)各种道德理论的方式都诉诸了这一观念:个人能理性地意愿的东西都预设了独立可理解的“有关个人所具理由以及理由相对强度”的观念(118)。这点把这些理论区别于康德自己的观点,也区别于某些重要的当代康德主义者(如科丝嘉)的观点。帕菲特承认,他依赖于一种原始且“不可定义”的理由,随之还承诺存在一种不可还原的规范真理,这使得他的观点成了某种被科丝嘉称为“独断的理性主义”版本。就此而论,它不仅受到如科丝嘉这样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者的抵制,而且【xxv】也受到倡导不同元伦理视界(outlook)(如某种形式的自然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的学者的抵制。
因此,帕菲特在第六部分承担着这样的任务:解释并捍卫自己的规范性观点。他把自己认同的观点称为“非形而上且非自然主义的认知主义”。这种观点诉诸我们对“不可还原的规范真理”具有的某种直觉信念。这种观点并不主张存在某些非时空的实体(reality)成分,在此意义上,它不是柏拉图式的。此外,它对直觉的依赖并不是用来表示:规范事实是通过某种类似于感官感觉的精神能力而理解的。我们也并不把像正当性和合理性这类规范属性的出现看作是规范事实因果影响的结果。相反,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规范真理的理解方式就像理解数学或逻辑真理的方式那样。帕菲特实际上主张,数学推理和逻辑推理本身就包含认识到“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的规范 真理,且要对之做出回应。例如,我们承认真理p,且“如果p,那么q”,这就给了我们结论性的理由相信q。帕菲特坚持,正如存在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何事的真理,也存在着我们有理由做何事的真理。
当然,帕菲特也意识到,许多哲学家并不接受“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不可还原的规范真理”。虚无主义者和谬误理论者都认为,一切规范主张都是假的(false)。自然主义者认为规范事实可还原为自然事实。非认知主义者则认为,尽管规范主张在人类生活中很重要,但它们根本不作为事实性陈述起作用。对于这些立场,帕菲特讨论和批评了其中许多有影响的版本,包括布莱克本(Blackburn)、布兰德特(Brandt)、吉巴德(Gibaard)、黑尔(Hare)、麦基(Mackie)和威廉斯(Williams)等人的观点。他主张,这些理论没有一个能够恰当地解释我们思想中的规范性维度;基于所有这些观点,规范性都被证明是种幻觉,消失不见了。实际上帕菲特看来认为:所有这类观点都倾向于虚无主义,且对于承认不可还原的规范真理来说,虚无主义是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科丝嘉对规范性“实在论”的康德式反驳也说服不了他。与科丝嘉强调的相反,他声称规范性的根源并不在于【xxvi】意志,反而在于不可还原的(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什么、想要什么和干什么)规范真理的存在。
正如马上会明朗的,帕菲特讨论理由与规范性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讨论实质性道德理论时所追求的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的目的是证实公认对立的某些理论实际上是趋同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表面分歧就会消散。但是在讨论有关理由和规范性的不同观点时,他并不把竞争理论之间的趋同性纳入议题范围。他相反主张,我们应该接受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拒绝基于欲望的理由理论。同样,我们应该接受他的认知主义理论而拒绝一切形式的自然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理论。帕菲特明显受困于实质的道德分歧,因为他认为这会威胁到我们对存在道德真理这种事情的确信。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如此强的动力,要去证实各种相竞争的道德理论具有趋同的可能性。他尽管也受困于元伦理或元规范的分歧,但反应是大不一样的。在此他只是简单地试图决定何种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帕菲特试图证实会趋同的各种理论都预设了他有关理由与规范性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显然是有争议的,这就会让我们质疑他所描述的实质层面的那种趋同性是否真是重要的。对那些拒绝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的人,或者对那些接受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或建构主义的人而言,这种道德共识所依赖的元伦理学观点恰恰是他们所要拒绝的,故而是无法打动他们的。因此,帕菲特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证实他所力证的这种趋同性,其重要性不会被它对有关理由和规范性的(不存在任何趋同性)主张的那种依赖所破坏。帕菲特尽管没有直接应对这个挑战,但确实主张:人们之所以拒绝他所偏爱的那种有关理由和规范性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对其观点并没有充分的了解。他表达了这种愿望:一旦相关的误解得以消除,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最终会接受这些观点。如果此论不谬,即便理由和规范性的相竞争的理论本身【xxvii】并不趋同,我们也有理由指望,哲学家对这些理论的评价上会有越来越大的趋同性。当然,这个建议本身就很可能是有争议的。
对于帕菲特精细微妙的论证,我们还能且会提出更多其他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帕菲特试图证实会趋同的各种道德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是其常见观点的真实版本。四个评论者均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了讨论。康德式契约论在何种程度上是真正康德式的?我们已经看到,就合理性与理由之间的关系论说而言,这个观点看起来更像是帕菲特的而不是康德的。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对其他表面趋同的立场提出来。斯坎伦式契约论在何种程度上是斯坎伦自己的观点?帕菲特的规则后果论版本与其他的后果论表述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正如斯坎伦提到的,帕菲特非常直率地承认,在发展“康德式”立场时,他乐意偏离康德的实际观点,只要他认为这有助于改进它们。如帕菲特所言,“我们在问的是,康德的公式能否有助于我们决定哪个行动是不当的,能否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这些行动是不当的。如果我们能以显然必要的方式修正这些公式,那么我们是在发展某种康德式的理论”(298)。在对斯坎伦的回应中,他同样明确了这个事实:他对于康德式契约论与斯坎伦式契约论的趋同论证“并不适用于斯坎伦书中陈述的观点”(卷二,244),相反是适用于在他看来是这种观点经过修正而加强了的版本。
这种不认错的修正主义给帕菲特带来了两种风险。斯坎伦提到的第一种是,他能证实的任何趋同有多么让人吃惊和多么重要,取决于趋同的各种理论与它们的理论原型有多接近。修正的方式越大,理论离原初表述越远,那么这种趋同就越不令人吃惊,也越不重要。第二个风险是修正原初理论让它们更为接近时,我们有可能排除掉了原初理论有价值的成分。
【xxviii】沃尔芙看来很是认为帕菲特的趋同性主张同时有着两类风险。就帕菲特试图调和康德主义、后果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抱负而言,她写道:“只要上述所引话语是意图表明,这些不同传统所强调的价值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诠释和排序,从而可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张力,或者说本着这些传统最伟大的倡导者的精神来接受对所述观念的修正和限定,从而最终与其对手和平共处,那么帕菲特就偏离了他所讨论的哲学家的明确立场,这种偏离方式在我看来既在诠释上是讲不通的,在规范性上也是令人遗憾的”(卷二,32)。沃尔芙的观点是:康德主义、契约论和后果论传统各自有着相异的评价性视野,每种视野都有重要的贡献,但它们彼此之间确实有着真正的张力。这些张力反映了我们道德思想本身之内有着更广泛的张力。她认为,就此而论,无法消除这些张力也是用不着遗憾的。帕菲特试图寻求的那种统一原则将必然是个妥协而不是趋同的问题,并且任何这样的原则必然会遗漏某些重要的价值。沃尔芙特别参考了帕菲特的康德主义版本来强调最后一点,她认为,这种版本限制了自主性在康德本人的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性。
赫尔曼也认为,帕菲特的立场在根本的方式上偏离了康德的立场。然而,尽管沃尔芙怀疑帕菲特寻求的“道德依赖于统一原则”这个观念本身,但赫尔曼赞成康德自己的统一性论说,还认为帕菲特的理论是不同成分的不稳定混合。更具体地说,她认为帕菲特采用了一种“杂交”方法论,纳入了一些康德主义的特征,但尽管如此还是具有强烈的后果论色彩(卷二,81)。尽管帕菲特的意图是保持康德观点中最有说服力的成分,同时避免其中显然不得人心的含义,但赫尔曼还是认为:在康德主义与后果论方法论之间的“不匹配”是深刻的,试图组合它们必然会扭曲康德自己的论说,还会遮蔽这种论说中最有吸引力的成分。在其评论的第一部分,她确定了【xxix】帕菲特方法论中的几种成分,认为它们具有深刻的后果论特性,然后她对她看到的帕菲特与康德在方法论上的分水岭做了阐明。也许最基本的差别是这一点:帕菲特诉求了各种非道德善来决定我们可以理性地意愿什么,然后依此来决定道德的内容,然而,赫尔曼说道,康德则是试图在一个独立地确立的道德框架内来确定非道德善的地位。在其评论的余下部分,她试图证实,“统一的”康德式进路如果得到恰当发展,那么就有办法纳入康德看来忽略了的某些最重要的道德直觉——诸如有关可允许的谎言的直觉。如果此论不谬,那么我们想要一种混合的道德方法论的动力就被大大削弱了。赫尔曼颇费苦心以这种方式发展统一的康德主义观点,对此帕菲特在其答复中未予直接回应。然而,他拒绝赫尔曼对他的方法论与康德方法论“不匹配”的评价。他强调,赫尔曼所引其明显的后果论方法论中,实际上大多数方面也是康德观点的特征。尽管他对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确实做出了修正,但有些修正是完全本着康德主义观点之精神的,还有一些则是为了避免一目了然的错误。帕菲特认为据之可得出,他与康德在立场之间的差距,远没有赫尔曼所声称的那么广泛和深刻。
像赫尔曼一样,伍德也主张帕菲特的哲学方法论在诸多重要的方面都与康德相背离,但与赫尔曼相比,他更注重帕菲特在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伍德认为,帕菲特的方法论起源于西季威克,这种方法给自身设定的目标就是提供一种“科学”的伦理学。这种想法是要把我们常识性的道德意见系统化,有必要时做出修正,其目的在于得到一组确切的原则,由此对于个人在一切可设想的环境下应该如何行动可以用某种算法得到一个确定的道德裁定。伍德认为如康德、边沁和密尔等人本来就是非常不同的哲学家,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法,他本人认为这种方法要优于他归于西季威克和帕菲特的那种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始于道德常识,而是【xxx】始于某种阐明基本价值的根本原则。一般性的道德规则或义务是由此非演绎性地从根本原则派生出来的。这些规则或义务代表了某种努力,其目的在于诠释人类生活条件下的根本价值之蕴含。规则或义务本身容许有例外并且要求诠释:它们在应用于特定情形时需要我们做具体的判断,而无法以确切的规则或原则去规定。因此,如伍德所理解的康德式方法一方面不像西季威克式方法那么重视常识性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它认为没有希望达成这样的目标:建立一种能够提供某种算法的“科学的”伦理学,以服务于道德决策。
伍德认为——尽管帕菲特的回应表示他不接受这种诊断——刚描述的这种方法上的差别构成了他与帕菲特在有关康德人性公式的诠释上产生分歧的潜在原因。伍德还认为,这种差别也使得他们对于一种常见类型的哲学论证表现出泾渭分明的态度。这类论证使用我们对某种程式化且有时很复杂的虚拟例子的直觉反应来检验各种道德原则。所有这类例子无论是否涉及实际的列车,伍德都称之为“列车问题”,以揶揄地致意于由富特首次引入哲学文献的这类著名情形。帕菲特频繁使用此类例子来建构他的论证。例如,他对康德主义与规则后果论的趋同就极为依赖这种主张:在一种行动方案会给行动者自己带来负担且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给别人带来负担这样的情境下,个人能够合理地同意什么。帕菲特用一系列虚构例子(大量不同的虚构环境会给不同的人带来负担,其类型不同且程度不一)来阐明和捍卫他的主张。他试图在这些例子中引领我们道德上的直觉反应,以表明:(1),每个人都会理性地意愿后果论的最优原则会被普遍接受,即便这些原则会给自己带来负担;(2),不存在人们会理性地选择普遍接受的任何其他原则。帕菲特显然相信:使用虚构【xxxi】例子有助于澄清在复杂道德选择中的相关问题,并使得我们能够在道德论证中取得进步。相对比而言,伍德认为“列车问题”对于道德哲学一无是处(68)。他的论文的主要部分都在于对这种方式的一种广泛批评:依赖此类问题会把道德哲学家引入歧途。
只要其他人也像伍德一样,对在道德哲学中诉诸虚构例子持保留意见,那么帕菲特大量依赖此种例子就会成为人们抵制其论证的根源。当然,即便是并不像伍德那样完全拒绝此种诉求的那些人,也可能发现,在帕菲特讨论的某些具体例子中,其反应不同于帕菲特,尽管帕菲特已经预见到了许多潜在的分歧并且展示出力图消弭分歧的杰出智谋。然而,帕菲特自己也指出,人们对于某些情形的反应取决于他是接受基于欲望的还是基于价值的理由理论。既然他指望使用我们的反应来支持他有关不同理论趋同的主张,这种变量(我们反应上的分歧)便反映出一种可能:正如我们对规范判断性质的元伦理分歧一样,有关理由和合理性的分歧会产生威胁,乃至动摇他试图确立的那种道德共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帕菲特对于这种威胁的回应,不是在相竞争的元伦理学理论、理由和合理性理论本身之间寻求趋同,相反,他主张我们有着决定性的理由,可以拒绝“非形而上且非自然主义”的元伦理学和基于价值的合理性理论之外的一切其他选项。他把这种趋同的指望放在哲学家最终会接受他所偏爱的那种认知主义和基于价值的立场。这是消除分歧或说去掉心头之刺的另一种方式:证实只有一种立场是我们可以理性地接受的。
无论是通过理论的趋同还是通过决定性证实竞争观点的不足(inadequacy),汲汲于消除分歧是帕菲特著作的鲜明特征。有时候它表现为一种紧迫感。他对沃尔芙的回应就体现了这一点。沃尔芙把帕菲特看作是竭力【xxxii】表明“存在着单个的真道德,浓缩为单个的最高原则,不同的传统摸索着,且都是以自己独立且不完善的方式,走向它。”(32)相对比而言,她本人说道,如果“最终表明”道德没有这样一种统一的原则,“这也不是道德悲剧”(33)。帕菲特在回应中说,“如果不存在单个的最高原则,这不会是道德悲剧”,但如果没有任何单个的真道德原则,这将是一个悲剧。”他补充道,“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种分歧,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存在任何的真道德。这可能最终表明道德什么也不是,因为也许道德只是一种幻觉”(151)。也许正是前景“黯淡”的不祥之兆,乃至如其所担忧的“更黯淡”前景——根本没有任何重要之事,在帕菲特心头挥之不去,才能解释他消除分歧的那种紧迫感。无论是否赞同他对来自深刻分歧之威胁的这种估量,人们都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追求目标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非凡的创造力和纯粹智识的强度。他富有挑战性的大量讨论,通过与斯坎伦、伍德、沃尔芙和赫尔曼的交流之襄助而得以阐明,由此以新颖且不同寻常的眼界重塑了常见的争论,开启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新思路,从而可让哲学家做出更进一步的考察。只要人们对道德、规范性和合理性理论感兴趣,他们就无法忽略这本杰出的、发人深省且有着坚定主张的著作。
编辑:在远方写作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经译者葛四友老师授权,曾在2015年10月7日首发“节选”于微思客。今日特刊发《导论》全文,以飨读者。如需转载,务必取得授权。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