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你分得清吗?
童志超
在很多人眼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比较模糊的概念。甚至在一些强调“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别的人看来,前者也不过是后者的温和或积极版本,即当一国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自豪感是单纯地建立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对比上时,他们就成为了危险的民族主义者,而若这种感情本身没有包含过多的自我优越性成分,那么它就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爱国主义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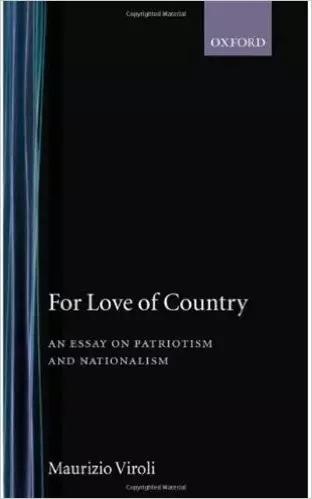
而由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当代新共和主义大师穆里齐•维罗里(Maurizio Viroli)于1995年出版的《关于爱国:试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For Love of the Comtry:An Essay o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则旨在彻底划清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词的界限。
全书通过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结合作者本人的理论剖析论述,澄清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本质上而非单纯程度上的巨大区别。
若考虑到在中国以“天下观念”为主导的漫长历史中,“国家观念”不过是19世纪以来的“舶来品”,这本探讨西方语境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历史变迁的经典著作也就同样值得每一位对国家民族问题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去仔细阅读。
维罗里首先在书中表明了”Patriotism”(爱国主义)和”Nationalism”(民族主义)诞生时期上的差别。”Nationalism”是在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初步建立后才有的思潮,距今不过不到300年的历史。与之相比,”Patriotism”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古董”,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希腊。”Patriotism”一词源自拉丁语中的”Terra Patria”,意为“父辈的土地”(Land of the Fathers)。
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下,”Patriotism”是一种对自己城邦高度虔诚的宗教式感情。毕竟在那个城邦竞争中败者将惨遭屠城的年代,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都依赖于城邦的存续,他的命运也就因此是与城邦前途近乎一体的。
到了古罗马共和国时代,这种个人与城邦间高度认同被公民与共和国间的认同所取代,”Patria”也就有了”Republica”共和主义的含义。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Cicero)最先将爱国主义和捍卫自由,秉持法治的共和政体联系在了一起。爱国主义成了共和国“共同自由”(Common Liberty)的代名词,是反对寡头独裁政府的思想武器。
这种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观在随后的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著作以及欧洲普通市民的人文主义的叙说中也都有所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政治思想奠基人马基雅维利(Macheavelli)在15世纪对共和式爱国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由其撰写的《佛洛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对”Patria”和”Nazione”,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词源做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在性质上而非程度上的区分。”Patria”就是以捍卫共同自由和共和制度为代表的公民美德(Civic Virtue);而”Nazione”则指当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各自特有的文化习俗,且尤指那些导致社会腐败堕落的“伤风败俗”。
这就顺带引出了维罗里全书的主要观点,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忠诚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情感。前者所热爱的是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石的共和政治制度,它是高度政治性且与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后者所效忠的则是一套统一的文化习俗,其本身是非政治(Apolitical)或先于政治(Pre-Political)的。
随着17世纪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大陆的建立,“爱国主义”开始逐渐丧失了其共和主义的属性。绝对君主国家不是共和政体。其最高统治者也就因此必然要对爱国主义思想进行改造,用对国家或君主的无条件忠诚去替代原先的对共和制度和共同自由的热爱。不过维罗里也指出,即便王权时代的欧洲还是出现了几个如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荷兰一样的共和国,传统共和式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就在这几块还算具有政治自由的土地中存活了下来。
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主义时代,爱国主义的共和话语也就在共和政治思想的全面复兴下重回欧洲大陆。维罗里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卢梭(Rousseau)等思想家的经典作品中对爱国主义的探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恢复了爱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和马基雅维利一样,他也把爱国主义描绘成对保卫共同自由的制度和法律的热爱。而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等作品中,卢梭同样把爱国主义视作一种政治美德,即捍卫我和我的同胞在共和国下所享有的共同自由。不过在《波兰政府论》中,卢梭改而强调了国家文化习俗等非政治性元素的重要性。虽然在维罗里看来,此举只是卢梭因波兰时刻可能被周边邻国吞噬的特殊国情而不得以而为之出的下下策,但这种从共同自由之地到文化精神统一体的转变,经过18世纪末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等浪漫主义、反启蒙思想家的“扩大化改造”,就产生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换句话说,《波兰政府论》中的“文化模型”的民族主义逐步盖过了《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模型”的爱国主义。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最终促成了爱国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全面过渡。国家情感由对共和自由制度的追求转变为精神、文化和民族在国家层面上“排外性”的统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后人们对传统共和式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欧洲进入帝国扩张时代后统治者出于利益需要的有意而为之的结果。殖民体系下爱国主义中对共同自由的追求和由此可能引发的对被压迫地区人民的同情是会威胁到既有政治秩序的。于是,欧洲各国的统治精英们便纷纷选择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用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同质性去替代共同自由的普遍人性解释,最终将共和式的爱国主义观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
一直到了20世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伤亡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灾难后,人们才重新清醒意识到了为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所带来的巨大恶果,爱国主义的传统含义也就又被“请”了回来。为很多人所熟知的,由当代欧洲首席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无疑属于当代复兴爱国主义思潮的代表。
在维罗里看来,虽然哈贝马斯因个人的一些误解(把共和主义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非发展成属于古罗马共和国的思潮)否认了其思想与共和主义的内在联系,但“宪政爱国主义”本质上非常接近于一套传统共和式的爱国主义。和前面对共和式爱国主义的相关论述一样,“宪政爱国主义”分清了政治性(宪法原则和政治制度)和非政治性(文化、民族、风俗)的概念,并认为爱国者所要忠于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在全书的最后部分,维罗里再度强调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所蕴含的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道德要求。一个在民族和文化意义上都很意大利式的意大利人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却可能因其政治冷漠或者腐败行为而不能称上一个合格的爱国主义者(作者维罗里本身是意大利人)。反之,一个民族和文化上都非所在国主流的个人也许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但却可以凭借其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而成为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总的来说,爱国主义不包括民族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它甚至不要求一个人在民族和文化上产生与同国大多数同胞间的认同,它的核心含义依旧应该是其传统共和主义式解释,即去作一个追求和捍卫政治上共同自由的合格公民。
(图文编辑:刘彪)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